《難不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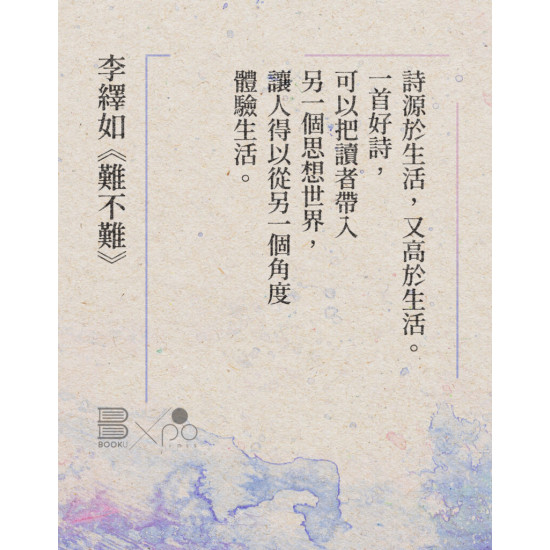
《難不難》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以上是初唐詩人駱賓王於七歲時所作的《詠鵝》。寥寥數字,就繪聲繪影地寫出了一群白鵝在池中戲水的形態;無論是遣詞,抑或是對仗,俱十分精妙,合該成為後世萬千學童的啟蒙古詩。
詩難嗎?答案因人而異。
前陣子,我在臉書上看到一篇句句鏗鏘,字字血淚的文章。那是一個高學歷家長對小學華文課程編委會的不滿,更是她對整個教育制度的控訴。那段日子,我整個面書就像是個線上吐槽大會,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訴說著自己對課文內容的不滿;又像是個大型辯場,正反方辯手都說得義憤填膺,各方辯詞也一般頭頭是道。最後還引出了「華文難否」,這個極具爭議的課題。
家長對課文或考題有所不滿,早已不是新聞。廿餘年前,我還在上小學時,就有一樁 “水牛與黃牛” 的公案,至今仍未了結;然因事隔多年,且其中一位當事人早已告別杏壇,該案也只能不了了之 。
也許因為當時科技並不發達,“水牛與黃牛” 一案未在校園掀起多大波瀾。大部分家長雖為孩子叫屈,卻也只能自嘆倒楣。我母親的反應則較為另類;還記得她當時拿著考卷,皺著眉頭研究了老半天,之後又與從事教育工作的姑母討論了老半天;而原該是 “受害人” 的我,卻只能忐忐忑忑地待在書房,強迫自己靜下心把功課寫完。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一家人用過晚餐,母親才拿著考卷和一本少兒雙語圖畫辭典,極有耐心地與我解釋了水牛與黃牛的區別,再讓我背了各種家禽家畜的三語單詞。
到後來,我才知道兩位長輩把我那次失誤歸咎於我貧瘠的詞彙量,一致認定那是我在考試時沒想出 “Buffalo” 一詞的主因。
那一年,我八歲,和臉書上那位氣急敗壞的女士的孩子同齡。
八歲的我若看到了那篇文章,一定非常羨慕,甚至還有一丟丟妒忌。
倘若時光可以倒流,回到那個懵懂的年代,我大約會想探問這二位長輩不為打抱不平的原因。 當然,這也只是一種痴想罷了。
不久前,我那備受寵愛的四歲侄女正式開蒙。
為表重視,姑母率先贈送了全套兒童中英繪本;我則按著自己的軌跡,與嫂子推薦了幾本幼兒唐詩。豈知,得到的答覆竟是「太難了!」
詩難嗎?這道題,我想我答不了。
自打有清晰記憶以來,我的生活似乎都離不開詩。因中文並非我的第一語言,初上幼兒園的我並不懂得與同學相處,而園裡的是華文教育。母親為鍛鍊我的閱讀能力與口語水平,便決定教我念詩,並把詩文融入日常。而開篇所提及的那首《詠鵝》,便是我最早接觸的其中一首古詩。
古詩,離我們並不遙遠。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這句已然成為最熱門愛情誓言的名句,就是出自《詩經·邶風·擊鼓》。
《詩經》,是中國古代詩歌的開端,中國文學史上最古老的一部詩歌總集;其中的 “十五國風”,正正是上古時代十五諸侯國的民間歌謠。由此可見,詩原非文人士大夫的專利,亦非死沉沉的教科書,更非硬繃繃的考試範本,而是人民生活與思想的結晶。
詩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一首好詩,可以把讀者帶入另一個思想世界,讓人得以從另一個角度體驗生活。譬如《葬花吟》,成功地塑造了一個孤傲感性的林黛玉,也充分地展現她面對生命的迷茫與無助;《柳絮》則描繪了一個世故圓滑的薛寶釵,巧妙地透露出她的人生志向。
然而,令人嗟嘆的是,自詩詞被納入教學課程以後,就已經成了一篇篇緊箍咒,拘束了學童自由的想像力,綑綁了本該奔放的思想。
我想,家長們所懊惱的並不儘然是課程的難度,更多的是改變所帶來的無措與無力感。
制度,讓我們都習慣了從課文中找尋答案,卻忘了人生並沒有標準答案。很多時候,標準答案就像是令人成癮的嗎啡;雖能一時紓解我們對未知世界的恐懼,卻也麻痺了我們的好奇心,遲緩了我們的探索欲。多少人清楚知道治標之法終非長久之計,卻還是無法自控地深陷其中。
我很慶幸在我求學的路上,父母不曾與我過多的保護,也從不為我設下任何條框,還身體力行地告訴我何謂自強不息,迎難而上。
華文難否?
我不會刻意煽情地說天下至難,也不會避重就輕地說非常容易。
事實上,學習從來就沒有捷徑,更沒有止境。那是一個持續尋覓與求索的過程;當中有荊棘也有花香,還有淚水與汗水。可是深藏其中的瑰麗與磅礴,無以倫比!
#BooKu
#品系
#八月專欄
#稱心如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