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樣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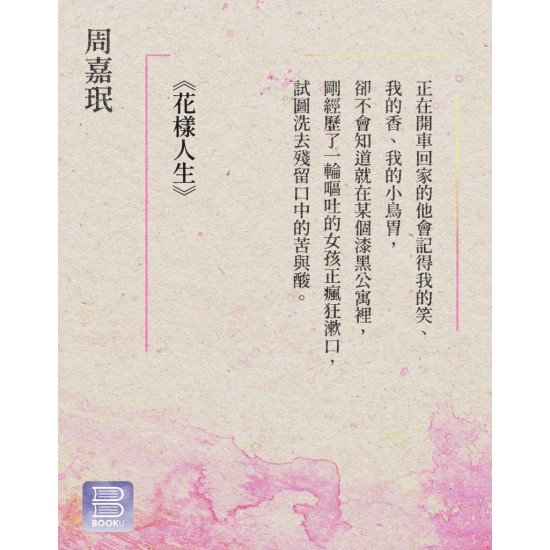
大約是睡房陳設太過懷舊,我近幾個星期總是夢見中學時的事。倒不是大考,我最不怕大考,就只怕黑和怕鬼。雖然很多舊同學都說最恐怖的是荒廢科學實驗室的標本櫃裡的嬰孩標本。
我是中二那年加入的華樂團。新成員就是金字塔最底層,其中窮的、醜的、胖的則是最底層中的更底層。在更底層裡,女孩又要比男孩更低一層。這一層的女孩從不被允許出錯。尤其是合奏的時候,一房間的團員忍著疲累疼痛,撐完一曲又一曲,就等著負責指揮的學長滿意點頭。結果就因為一個最底層中的更更底層快了還是慢了,某個音歪了還是斜了,所有人就得陪著留堂挨罵。其實被學長當眾用指揮棒指著來罵也並不算什麼,可怕的是周圍那些刀子一樣的目光。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那種四面楚歌的恐怖與絕望,直到若干年後在教會裡看了電影《耶穌受難記》裡搬演的耶路撒冷十四處苦路才哭得一塌糊塗。
儘管體無完膚,但我仍未死。真正把我釘上十字架,使鐵釘穿透我四肢骨骼的是「失格」。
班上有位樂團敲擊組的女同學。她有一頭我十分羨慕的直頭髮,還有一副我萬分羨慕的瘦削身材。同樣的校服,她穿上身是筆挺俐落,而我就只有說不完的彆扭與尷尬。我總是癡妄地以為只要把頭髮燙直,少吃多運動,醜小鴨終會長成天鵝。殊不知在那位同學所代表的金字塔上層人的眼中,我始終沒資格——沒資格與她們交朋友,沒資格與男同學說話,也沒資格打扮。
我趁年底長假開始地獄式訓練,一口氣減了一個小學生的重量。換了一副身軀就好比換了一場人生,連帶著命運也改寫了。逛百貨公司的時候不必擔心因為穿不上牛仔褲而被銷售員恥笑,上學的時候也不再害怕面對女同學的眼光和男同學的搭訕。
如果這只是一部電影,故事來到這裡就該結束。可惜我不是電影女主角,不是人們期望中那個讓人剝光脫淨以後仍能維持標準八顆牙笑容的芭比娃娃。我很該健全,但造物主偏忘了給我的腦安上暫停鍵與取消鍵。死而復生所帶來的痛快與歡欣維持不到一個月,剩下的就只有無止境的蒼涼。
因我清楚明白我往後餘生所擁有的好人緣與好運氣都建立在我的輕減之上。皮相能夠長久依恃嗎?我情願相信那些男孩都是善良的,只是從前我的雙眼都被脂肪蒙蔽了所以看不見他們。
赴約前,我會抹上時尚雜誌推薦的最新款潤膚霜,畫上專櫃小姐教給我的號稱最受男士青睞的妝容,穿上新買的合身連身裙,然後笑著接受男伴的讚美,聽他說公司裡某位又胖又醜又不識趣的怪咖女同事。我會靦腆地笑說,“你太壞了!”,然後將只吃了一半的餐盤輕輕推開。我還會像愛情片女主角那樣對他說,“我今晚很高興”,再翩然推門走進公寓大堂。
正在開車回家的他會記得我的笑、我的香、我的小鳥胃,卻不會知道就在某個漆黑公寓裡,剛經歷了一輪嘔吐的女孩正瘋狂漱口,試圖洗去殘留口中的苦與酸。她望著梳妝台上的瓶瓶罐罐和印在卸妝棉上的容顏,想起小時候讀過的某個聊齋故事裡的青面獠牙,似曾相識。
牧師娘總會溫柔地摟著我的肩,耐心地鼓勵我讓我別灰心,因我們都是耶和華最寵愛的兒女,是按照祂的形象所創造的。我都聽著,但也好想問問,上帝會是個胖子嗎?看瑪利亞多端莊溫婉,假若瑪利亞又胖又粗俗,還會否被揀選受聖靈感孕誕下耶穌?
我決不回頭望。因為那個我就和舊同學口中很恐怖的嬰孩標本一樣,被封印在化學藥水之中,永不超生。僥倖還陽的那個我已成了冷血劊子手,將那些人與事一一敲進方塊文字裡。我這部13寸筆電就是他們的最後歸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