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流水般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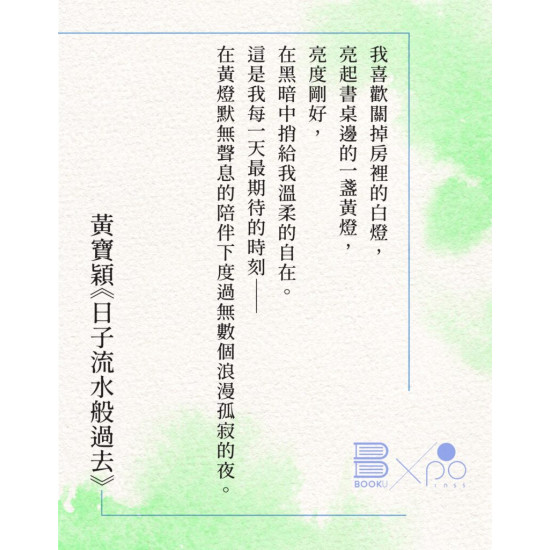
《日子流水般過去》
前天在家工作結束後,突然一陣暈眩,本是計劃給學生上網課後,繼續批改作文,結果眼皮子忽地沉重起來,似有無形的手爪子在使勁揉捏我的腦袋。我旋即下樓喝了杯溫水,說是溫的,其實有些燙手,許是我喝慣了熱水,入口時溫度還是剛好的。母親在耳邊說話,大概是記得吃晚餐、早些洗澡、幾點還上課之類的問話,但那聲音環繞於耳畔,卻彷彿遠在山邊,輕飄、悠遠起來。我許久都不答話,直到母親往來於廚房與客廳幾回,我才反應過來。
啥?你剛才說什麼?吃飯嗎?
母親瞪了我一眼。
隨意扒了兩口飯,我又上樓去了,打開電腦,端坐於筆電前,正要開始工作,那幾隻魔爪又來了。我閉上眼,一手托腮,心想小休一會兒總會好了。再睜開眼時,眼皮已抹上了一層麥芽糖,緊抓著對方不放。我扭了扭頭,發現筋骨竟是那般酸痛。
不對勁了。渾身不舒服。
起身往床撲上去,卻還不能睡去,便把筆電的插頭給拔掉,想起還有一部劇得認真追完。我喜歡關掉房裡的白燈,亮起書桌邊的一盞黃燈,亮度剛好,在黑暗中捎給我溫柔的自在。這是我每一天最期待的時刻——在黃燈默無聲息的陪伴下度過無數個浪漫孤寂的夜。
我已忘記看了多久的劇,沉沉睡去時,許是已午夜。窗外刮來北風,即使窗戶緊閉,我依然能聽見她的召喚,清晰、好聽。那一夜,我無法安睡,魔爪離去了,來了鬧騰的腸胃,幾乎折磨了我一宿。
隔天早晨,房裡的黃色小雛菊依舊可愛,醒來時把它拿到樓下去換了瓶涼水。我早起習慣喝豆粉搭配麥餅,但那天胃口特別差,吃得不好。
早晨有一場網課,學生是個可愛的男生,他常常與我說他和家人、朋友間的小故事,他愛說,我愛聽,成了支撐我倆完成漫長網課的樂曲。起先還好,後來那幾隻手爪子又來了,我強撐著精神給他完成了課堂,原本答應與母親吃素食午餐的約會也取消了,我對家人說,我好像病了。
那天是周末,常去的診所沒開,一整日昏昏沉沉,連畫也沒法畫,只能聽著音樂翻來覆去地睡著。我感覺體溫升高了,嘴越髮乾澀,骨頭硬邦邦,一動彈便發酸。所幸前一天換了床單,剛曬好的床單上殘留陽光的氣息,我才能稍有暖意地睡去。
那日晚餐時間是大哥叫醒我的,他買了我愛吃的麵條,我還是有胃口,餓了一下午,我吃得匆忙,母親還切了顆水梨要我一塊不剩吃完。
隔日起來,燒退了,步伐還是漂浮不定,於是我去了診所。車子停好,艷陽下我發現手機落在了家裡,沒法給停車費。急匆匆掛了號,我站在診所外被陽光洗禮,眼神不斷擺放在車子上。在我猶豫著是否要與隔壁的病人借手機付費時,我聽見了我的名字。相熟的醫生給我開了藥,他叭叭叭說了一堆話——口罩的隔層,我精神的渙散,不曉得是哪一個,總之我聽不見他說的內容,只知道點頭。
回家後,我拿出幾袋藥,五顏六色,此時,這種繽紛的色彩使人反胃極了。還是得嚥下去。
那天母親熬了白粥,煮了苦瓜,炒了雞蛋配上大蔥,溫暖了我一天的胃。
房裡的雛菊還是艷麗,我把她的葉子拔光了,在無依無靠下,她的生命力尚且旺盛,有了家的陪伴,我更不能隨意倒下。尤其在這疫情肆虐的敏感時期,保住自己,便是保住了時光裡的安詳。
#BooKu
#品系
#深夜專欄
#牆角的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