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接再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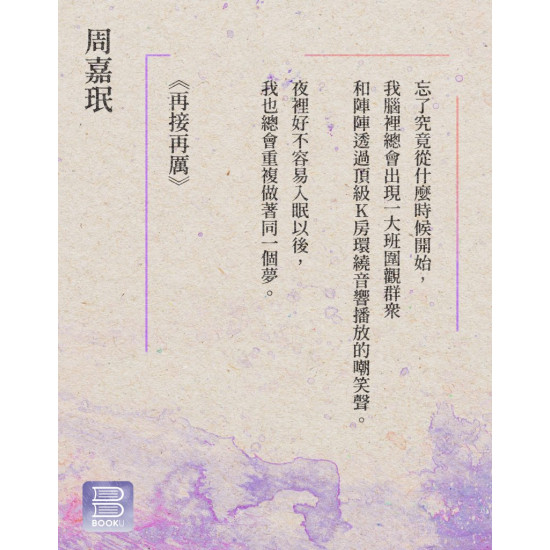
上星期整理筆電的時候發現了不少我大學時期寫的舊文章。
我一向害怕閱讀自己的文章,總覺得那樣很矯情,也很自戀。我甚至還有些害怕在報刊看見自己的文章,雖然我自中學開始就有投稿的習慣。除此之外,我也很害怕讓認識的人,尤其是熟人,看見我的文章。正因為這些莫名的恐懼,我很擅長給自己取筆名,也很有意識地避免長時間使用同一個筆名。
筆名於我而言就像是金鐘罩鐵布衫,透過各個筆名發表作品,我似乎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忘記或說服自己那些文字,不論好壞,一概與我,周嘉珉無關。這樣一想,我也就莫名地感到安心。反之若使用本名發表文章,我非但如坐針氈般難受,還會產生一種在大庭廣眾下赤身裸體的羞恥感。總覺得所有人走躲在我看不見的地方竊竊私語,議論批評。
這種“隱姓埋名”的日子隨著我近年加入「越讀者」面書社群,並參加「全民閱讀」公開徵文活動而到了盡頭。我本以為自己早已克服了恐懼,再也不必藏藏匿匿,但原來我離“撥雲見日”尚有一段不遠也不近的距離。
忘了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我腦裡總會出現一大班圍觀群眾和陣陣透過頂級K房環繞音響播放的嘲笑聲。夜裡好不容易入眠以後,我也總會重複做著同一個夢。夢裡的我一會兒回到金光燦燦的小學,一會兒回到鬼影幢幢的中學。但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不是個允許鬆懈的地方。無論是多麼耀眼的成績冊,教師評價那一欄永遠都是“勤能補拙”、“再接再厲”、“百尺竿頭”之類的話。
其實那都是老師的善意勸勉,但日子久了心中難免疑惑。我當時就總在想究竟還要多努力、多拼命、成績還要多好,才能得到老師一點欣慰的眼神和一句簡潔的 “well done”。
考上家中長輩理想的中學那年,我姑姑特意請了她一位書法家朋友給我寫了一幅字。那副字至今仍完好地貼在書桌上。每當我拿起筆電準備寫稿,那句話就準時地在我耳邊響起、迴旋。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
書架上總有讀不完的書,日程上也總有寫不完的文章。我不敢停歇,大約也沒資格停歇。廿餘年過去,我仍沒法忘記姑姑的耳提面命:就在你停下來休息享受的時候,別人早就溫完書,準備上才藝班了!
最近這種焦慮感又回來了。我比以往更頻繁地陷入自我懷疑與自我批判的惡性循環之中。我倉皇地把自己丟進小川糸筆下的海濱古都裡。但故事總會完結的,治標之法也只能夠帶來片刻美好安逸的錯覺。我總不能一輩子躲在文字構建的紙上鎌倉,一輩子不閱讀,一輩子不寫作。
昨晚睡前刷 Instagram 的時候又見人引用中島敦的《山月記》。
「我深怕自己本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磨;卻又半信自己是塊美玉,故而又不肯庸庸碌碌,與瓦礫為伍。」
多麼誅心的一句話!
行於天地間,若往前怕三步,往後怕五步,那就什麼都不必盤算了,還談什麼美玉不美玉呢!
人,終究還是要誠實面對自己,即使那將帶來十級劇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