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點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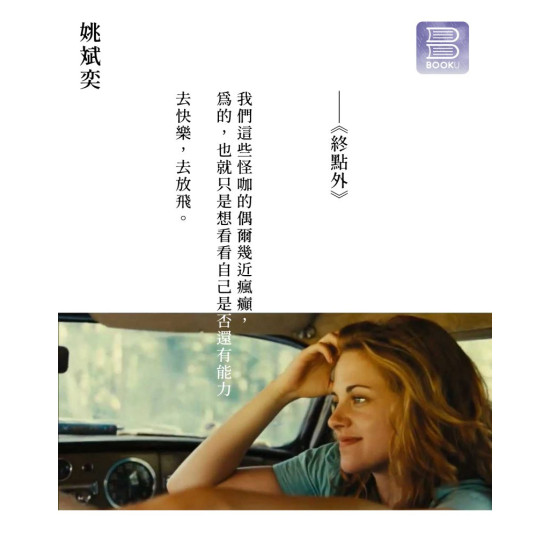
電影:On The Road 在路上
主題:終點外
《在路上》(On the Road),是一本曾經最為人熟知的流浪者文集。
這本書,誕生於二戰結束後的美國,由被譽為「垮掉一代」(BeatGeneration)的教主級作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於1957年成書。
關於《On the Road》,我首先接觸的是英文原版(圖書館借的),之後,再閱讀的便是中譯版——可以說,那根本就是兩部用著同一名字的作品。而導致這一結果的原由,實則就在於「垮掉的一代」,它是無法用約俗思想去瞭解的。我並不想要去批判譯者,但對於那些早已垂垂老矣的前輩旅者們,如果想要真的瞭解他們,興許真正的上路流浪,如台灣奇人作家舒國治,或觀看將其映像化,二零一二年上線,巴西人沃爾特.賽勒斯(Walter Salles)執導的同名改編電影,這會是更深入骨髓的唯二方式。
說到垮掉的一代,籠統上去看,那是一群在戰後蕭條中反叛游離的青年。他們生活簡單、不修邊幅,喜穿奇裝異服,拒絕承擔任何社會義務,並且大半輩子都以浪跡天涯為樂。他們蔑視社會的既定法規,反對一切世俗陳規和戰爭暴行,為了尋求新的刺激,他們總在強調絕對的自由,甚至往往,還會在旅途中以禪思,縱慾、吸毒、沈淪種種行徑,籍此向傳統的禮教標准宣示挑戰。
確實,在後人眼中如我看來, 書暨劇中的雙男主,薩爾.帕拉代斯(Sam Riley飾)和迪恩.莫里亞蒂(Garrett Hedlund飾),與他們的同伴以搭便車及徒步完成穿越美國之作法,在人類旅史上或堪稱標誌。以至六十年後的今日,他們當年所創造出來的無產浪遊思想,意識上也仍還在引導著一群又一群的年輕人們,於最無助失落時走向旅途。
但實際上這群人是否如公眾對他們的定論一樣,是生活的失敗者呢?
直至看完該改編電影以後,我更寧願去相信他們是在尋找,是在日復一日的拷問著自己的靈魂。他們渴望能在流浪中發現自己,瞭解自己,而一部分的他們,好比1974年到印度朝聖,1976年創立蘋果電腦的喬布斯(Steve Jobs),確實也真的在路上確定了未來的歸宿。於是到了多年以後的今天,直到他們已再次回歸久違的社會體系,他們的身體,縱然已不再漂泊,但他們的精神,卻是永遠都還會在路上的。
簡單言之,故事的主軸圍繞在了薩爾和迪恩,兩名「頹廢」青年的身上。一個憂鬱的文學作者,加上一個野性的帥氣嬉皮士,從加拿大蒙特婁至合眾國東西岸再至拉丁美洲,它們帶著妻子、情人與同好一路派對緊接派對,包括於荒野中盡情飲酒哈大麻的營火會,於各城市死黨們家中談詩論道的不醉不眠夜,於暫時定居點和男女伴侶多人運動的情慾週,於爵士酒吧隨樂起舞大汗淋灕的高昂分秒,還有於墨西哥拋妻棄子瘋狂狎妓的放縱日,導演用手搖鏡頭配合跳切剪輯,來表述人性另一面的魔嗔迷因——那些極樂狂歡下的強烈焦慮與不安。
不安,源自二戰後爆發的嬰兒潮,所引領的全球集體大亢奮,人們似打了雞血般,下意識的併入那飛速轉動的新經濟巨輪,但哪怕是如此朝氣蓬勃的時代,亦仍有一部分自覺被社會無視的邊緣小眾,這群人反主流價值逆行,崇拜有著毀壞特質的人或物,譬如薩爾一夥對迪恩魅力的盲目態度,按愛爾蘭文豪王爾德的說法:「從藝術的觀點來看,壞人是非常吸引的研究對象。他們代表了色彩、變化與特異。好人會激起人的理性,壞人則引發人的想像力。」
唯想像力畢竟不是無限額度的,它能驅使你我生出一萬個理由去好奇淪陷,但倘若提及心境上的成長,務實終究才是正軌。是以故事的尾聲,旅途後的薩爾總歸踏入出版界去經營自家作品,之間迪恩曾在一次業界晚會的場外等候他,欲說服他再次上路,可當筆挺西裝面對破舊夾克,哥倆的道路早是南轅北轍,拒絕婚姻、親子、工作等責任的迪恩,與擁抱現實的薩爾,他們的人生註定將無法平行。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on the road》實際上並不是一部如人們所想像中,含有「誤導性」,「教壞細路」的第二人稱自傳。就像流浪式的旅行一樣,也不僅僅是只有逃避而已。相對來看,我更願意去想信無目標的旅程是「希望性」的,是一種能讓內心去切確「融入」環境,自然與社會的行為。因此,我僅引此齣戲的一句開幕名言來略為說明:「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I knew there'd be girls, visions, everything; somewhere along the line the pearl would be handed to me.」(在社會標準這條線上,我知道某一個地方會有我要的女孩,理想,甚至一切。但沿著另一條路線繼續前行,我深信會有更珍貴的寶珠(暗喻人生)將交託予我」《本人自譯,詞不達意還請多多包涵》)。」
從這句話裡,我看見了一顆單純之心,也明白到了追逐自由的人,無論他們是「垮掉的一代」,還是如我們般,八零九零後的「20世紀末代」,本質上,都實則是拒絕被陳規擺佈的一群。
有時,我們確實會因為頭腦發熱而突然幹出一些很出格甚至很誇張的事。但我們的本意,卻並非想要去真正的「不負責任」,我們這些怪咖的偶爾虛榮,偶爾放縱,偶爾憂鬱,或偶爾幾近瘋癲,為的,也就只是想試驗一下那早已麻木的心靈,看看自己是否還有能力去快樂,去放飛。
於是乎,從種種的遊走測驗中,我們歷盡了自己的迷茫,失落與分裂。可同時間,我們亦在他鄉重啟了救贖,並且看見了久違的療癒契機。
而在這個你我都無語的年代,我們又該如何去定位自己的坐標?該如何去分辨什麼是理想而什麼是現實呢?
也許,答案就在路上。
也許,我們都已在終點外的起點上。
#BooKu
#深夜專欄
#戲子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