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境內,眾生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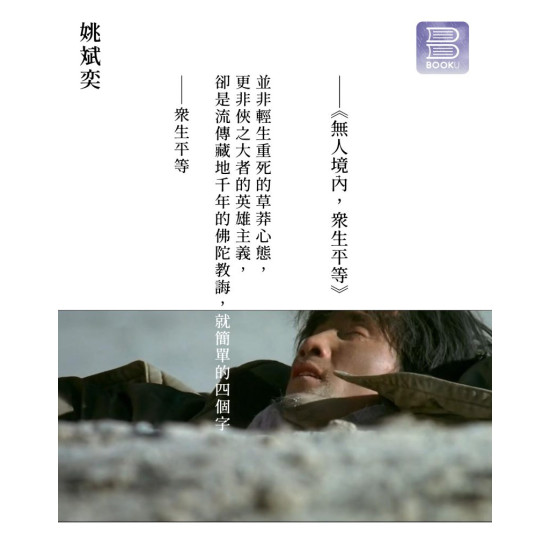
電影:可可西里
題目:無人境內,眾生平等
人生何去,向來是很多電影載體欲表達的終極命題。有的創作人擅長刻畫「死」之細膩,比如一眾日系法系導演,有的創作人則把「活」之真意拍出了新高度,比如一眾韓系華系導演,但要論兩極並重者,特別是讓人看了會重新思考「生死」本質的映像敘事,那就不能不提號稱中國學院派頭牌導演的陸川,以及他的封神之作——《可可西里》。
可可西里,一片位於今青海省西部的大面積高原台地,她是康藏人心目中的「 阿卿貢嘉」,意即「青山之王」,也是當前世間僅余下為數不多,萬幸還能避開文明侵擾的「無人聖地」。
說是聖地,因此處庇護了全球幾乎不可替代的多樣性生物資源,包括藏羚羊、野驢、野氂牛、藏狼、雪豹等等珍稀高原種群,這個群眾眼中氣候惡寒、供給匱乏、發展價值近乎零的「禁區」,卻恰巧成了動物們的繁衍「樂土」,成了能有效阻礙人類私慾腐蝕的一道天塹。
私慾是個什麼東西?《神曲》作者但丁說它的本質乃驕傲、嫉妒,貪婪三個火星,能使人心爆炸。而有關野生動物的皮毛,人們由於貪圖它的珍稀性,以能穿得起皮草為傲,並致令升起妒忌心的人去繼續消費——這,便是私慾的其中一種有力具像。
於是為了滿足國際奢華市場,對藏羚羊貼近皮膚的那層底絨,也就是時裝界趨之若鶩的「沙圖什shahtoosh」織品之需,從潛伏藏區四周的盜獵者,到私運羚羊皮出境的走私客,再到印度克什米爾邦的加工廠和新德里的交易黑市,最後隱藏於全世界的頂級精品圈,如此一環扣一環的非法收受,無辜的藏羚羊哪怕身處可可西里極地,亦究竟沒能躲過人心向利的荼毒。
言及藏羚絨,這款用了波斯語里代表國王的「shah」字來凸顯尊貴,隨便一件成品即可要價萬元美金以上的毛織物,不管是它的超細體積(直徑約11.5微米,人髮的五分之一)、超輕重量(單品不過百克),或它的超強防風密度(能抵禦零下嚴寒),縱觀其各個性能,實話講都是非常好的。唯是每完成一匹六尺布,就得殺害三隻野生活體,那樣的耗損亦著實太不人道,況乎藏羚羊還是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定義下的頻危動物,是故無論於法於情於理,捕獵和擁有它們都係一種犯罪,但此為題外話,興許下次補寫一篇,再表不遲。
回到電影本身,其背景設在了遙遠的1993年,那是個仍未盛行野生動物保育概念的年歲,什麼華南虎、金絲猴、白犀牛,今天我們為其慨嘆的物種,昔日只消稍稍值錢,人們說殺也就殺了,更別說這沒幾人曉得的藏羚羊,偷獵犯們殺起來真叫一個肆無忌憚。想必也是位不平則鳴的熱血男兒,彼時才剛初出茅廬的陸川導演,他沒和其他同行一樣去拍些掙錢的商業片,反之挑了「環保」如此個充滿人文關懷的題材,用孔夫子的話講,知其不易為而為之,人中大器也。
大器拍出來的畫面自然亦是大氣的,《可可西里》的第一幕戲,陸導便選擇了以赤裸裸的屠殺去反映實況——被圍殲的藏羚羊群,滿地血淋淋的剝皮屍體,一張張佈滿貪欲的「貨品」,偷獵者都說是為了謀點生計,但某些世代居住在該地的藏人們不答應,於此整部片子的主旋律逐漸循序清晰,那是兩種處事觀念之間的戰鬥,一方但求活好,萬物皆可欺,另一方則秉持信仰,與萬物一同枯榮,他們二者間的矛盾,往小了看是人性和道德的拉鋸,往大了看則是全人類之共業——君不見貴冑花錢,藏民付命,縷縷冤魂換絲絲羚絨的荒誕嗎?
由本地青壯自發組織的巡邏隊,他們不是警察,不是軍人,甚至連民兵都算不上,打著村工委會的名義,隊員們已經超過一年不曾從玉樹州政府處支倒任何薪資與武器補給,這種窘困,在那個改革開放初萌芽的時代,於許多內陸省份是司空見慣的。人人向前看,故此人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華南東南等沿海城鎮,那會兒地廣人稀的大西北到底承受著些什麼,生態環境到底破敗至什麼程度,沒人去想也沒人有力氣去知道。所以故事起始時,鏡頭就聚焦在了一名落單執勤的巡邏員,強巴的身上。他被盜獵團伙俘虜,被迫滿眶眼淚的看著盜賊們掃射藏羚羊群,隨著暗夜降臨,首領毫無預警的一槍結束了他稚嫩的生命,在可可西里,殺死一頭羊和殺死一個人的目地皆是求財。
然後畫面轉至其餘巡邏隊員的部份,他們從荒原帶回強巴的屍身,隊長兼全片主角日泰(多布傑飾),一個臉上總是皺著眉頭,盡是溝壑縱橫的中年男人,他正要替這枉死的藏族男孩舉辦天葬儀式。站在一旁觀禮,湊巧從北京來到青海採訪的尕玉,他以一個第三視角的姿態切入巡邏隊的日常中,那些盤旋啄食的禿鷹,那位手持法器法刃肢解遺體的天葬師,那個默默誦念的白衣少女,那一張張收繳於倉庫內的藏羚羊皮,於千裡外的國立圖書館裡,他一股腦兒都曾讀過。但此刻零距離的接觸著可可西里,他的陌生感卻是極其強烈的。
陌生,因他無法理解隊員們為何情願被拖欠薪金,也依舊要扛著幾把破步槍,冒著危險入無人區去追捕盜獵團伙。是出於強巴遭殺害的仇恨嗎?是出於對隊長日泰如父如師般的崇拜嗎?是出於藏民族對「阿卿貢加」的無條件信仰嗎?是在守護著祖祖輩輩與大自然的契約嗎?
或許上述的種種緣由都各有一點,但唯一無法否認的是,這群人生於斯長於斯亦註定死於斯,在他們的思維裡,可可西里即使再貧瘠,也還輪不到別的人來做賤。而尕玉不一樣,他的家在首善之都,他造訪此處的理由是為了完成採訪任務和理想,什麼山河湖泊,雲海風沙、白雪冰川,什麼羚羊氂牛、追捕盜獵、生死疲勞,他雖跟隨巡邏隊走進了無人區的心臟,可靈魂畢竟不屬於這裡,所以他只能拼了命的按下相機快門,用菲林去紀錄一次次局部無聲的悲歡離合,並冀望著今後讀賞照片的城市人與官老爺,能夠多少體會牧民們的刺痛,轉折設法中止殺戮。
是挺無奈的,他能理解日泰在路上設關卡,攔阻非法入侵者的意圖,他見證著他對同是藏民的盜獵者們實施罰款、燒車、私刑、拷問等等看似過激的舉措,也曾幾度質疑日泰是否濫權,仔細想想,尕玉就算懷抱使命,他亦畢竟是個現代北京人,他信奉的那套社會規範,包括同情心、法治和凡事協商等等文明約俗,順理成章的,也搬到了他看待可可西里的視角中去。然需知這是西北大荒,在貧瘠的高原上,道德教育沒有絲毫位置,生存才此處唯一的真理。
當然作為一齣電影,又怎能少得了撥動情緒的部份?之間有兩節戲便呈現得很棒,第一段,是巡邏隊出發到無人區執勤緝凶前,父母妻小們忘情的摟著隊員們訴說憂慮與關心,特別是日泰女兒央金的那句:「要活著回來啊!」,觀眾立馬便曉得,原來巡山人的每一次開拔,都是一次生死未卜的旅途,換言之,那一下下重重的擁抱,既是忐忑的生離,亦是說不準的死別。
第二段,是出行後一幫人在不凍泉邊吃飯時,突發的即興起哄。連綿雪山,伴隨著帳篷旁升起的裊裊炊煙,隊員小伙們陸續擊碗高歌奮力舞動,明日會否繼續站著他們不曉得,但此刻的愉悅和信心卻是肯定的,那強勁有力的步伐,那穿透遠古的節奏,局外人尕玉瞬息便理解到了生命的力度,在藏民的世界里,青春不是泡妞遊戲交作業,而是帶著先人的祝禱和對天地的敬畏,繼續哭笑決絕的活下去。
日泰必然也曉得自己的重大責任,一條條年輕的生命扛在肩上,他沒有無節制去展示仁慈的理由。因此他一旦鎖定盜獵者們,揮出的拳頭便總是不留餘地,可同時間他亦明白,這些持槍行兇的人們,本來也皆是老實巴交的藏族牧民,是資本家步步進逼的圈地開發,數年間便佔據了他們千歲承繼的牧場,這才導致一個個藏人落草為寇的。試想牛羊沒了,青稞田沒了,代之以的是與他們無甚關係的油礦、氣礦和沙漠公路,難道真的要遠赴上海深圳去做最低廉的勞工嗎?倘若不的話,除了盜獵又還剩下什麼活路呢?切莫忘記,如今的很多援助計畫,於舊日都仍未落定,這是每個發展中國家皆一律得經歷的陣痛。
就像劇中三番四次被寬恕釋放,卻依舊不懂感恩,反之倒過頭來出賣巡邏隊的盜獵者馬占林,他本是鄉里頭製皮技術最好的養殖人,且兒子還是名醫生,但九十年代突如其來的工業化衝擊,使得他短期內失去了全部草場,眼下他入夥盜獵幫派,專門負責給藏羚羊剝皮,按他自己的話說:「剝一張皮能掙五塊錢啊!」,由此得見在無助和貧困面前,馬占林這個於整條黑市交易鍊中,於上萬美金的終端銷售價里,區區只佔了五元人民幣的老漢—-坦白講,我真的找不到任何能怪罪他的理由。甚至倒過來他兒子還救治了巡邏隊小伙,該決定表明了馬姓一家絕不冷血,他們只是搞不清楚「打獵」和「犯法」的界限而已。
想來日泰跟你我觀眾是一樣的感覺,是故他縱然常有毆打盜獵者的舉止,卻從不真正要他們的命,除了走火入魔的首領,那是他獨獨恨之欲殺的元兇。事實上,日泰和巡邏隊常常也會有需要出售贓品的時候。例如整隊人被困風雪中,糧食彈藥汽油耗盡,成員肺水腫危在旦夕的一刻,他即當機立斷指派部屬劉棟,開著唯一仍未故障的吉普車回基地賣皮子籌錢換物資。這裡稍稍套進一個真人真事,曾就悲壯遭遇廣受外界關注的藏區「野氂牛」保育隊,他們的情況便是如此。在面積八萬多平方公里的荒野巡邏,單單每次出任務的汽油費已是近萬元,加上維修、職工食宿的開銷,靠政府給予的兩百元工資,實則杯水車薪。是以野氂牛隊漸漸的便和盜獵者們構成了一種微妙關係—-他們抓捕盜獵者,再買賣沒收的藏羚羊皮來補貼費用,照領隊扎西書記的解釋:「用已死去的藏羚羊來保護活著的藏羚羊,哪怕是殺頭,我也會主張賣的.......」
這樣兵不兵賊不賊的死循環,請問除了功利的官方和冷漠的財閥外,人們還能怪誰?
看看劉棟緊接的無奈決定,觀眾就大約可理會巡邏隊的悲哀。他九死一生趕往村子後,賣光了皮貨卻還湊不足物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頂著屈辱去和做小姐的女友要錢,陸川導演這一齣堪稱是神來之筆,一個巡邏隊員拿著底層女性的血汗肉金趕往救援戰友,都是資本巨輪下受壓迫的草民,他們不懂什麼「經濟局勢」,但他們懂得捍衛袍澤,捍衛家園。
往下劉棟誤闖流沙地,人和車子都被深淵吞噬掉,一若大自然從不對誰特別仁慈,可可西里的領域裡沒有善惡,只有悄無聲息的生命輪遞。再往下日泰也死了,死得頗具英雄氣概,他在孤身偷襲首領時被俘虜,面臨仇家環伺,他自始不墮志向,趁空隙一拳便朝首領臉上揍,他說我是幹部你是強盜,世上就唯有強盜伏法,沒有幹部求饒的理。
倒是盜亦有道,劇情裡記者尕玉的下場,和真實「野氂牛隊」發生過的事蹟吻合,盜獵者們獵羚是為了存活,殺巡邏隊員是為了阻撓他們「斷人衣食」,原則上,沒有殺尋常百姓的習慣,於是他們放走尕玉,於是才有了將來「可可西里」的深度報導。
還記得日泰提過:「我們藏人吃肉刀口對著自己。」,這句話多少解釋了牧民敦厚善良的本質。君可見卓乃湖畔,隊員們壘起藏羚羊的屍山,圍著熊熊烈火念誦,這正與戲里的開頭和結尾,也即強巴和日泰的兩場天葬儀式,本質上是遙相呼應的。於藏人來講,不管誰逝世了,英雄或平民,人類或動物,給予的尊重和待遇,包括祝禱的經文都會一樣,至此,你我終究明白什麼才是藏人們敢無懼殞落,且用命去保衛藏羚羊的倚仗了。
並非輕生重死的草莽心態,更非俠之大者的英雄主義,卻是流傳藏地千年的佛陀教誨,就簡單的四個字——眾生平等,在他們眼中救動物與救人向來無異。
導演陸川說:「可可西里,是天堂,是地獄,亦是見證生命與信仰的聖地!」
野生救援組織Wild Aid 呼籲全球:「沒有買賣,便沒有殺害」
我說關於生死,你我愚鈍,知之甚少,但不妨仰視雪域高原上的禿鷹,思考一下腐敗與高貴的差距——
鷹食腐屍,是大自然輪轉超生的意志,人著皮草,是千萬獸魂的血色憑依,結果孰髒孰淨,孰美孰劣,這不是明擺著的嗎?
#BooKu
#深夜專欄
#戲子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