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納森‧海德特,葛瑞格‧路加諾夫《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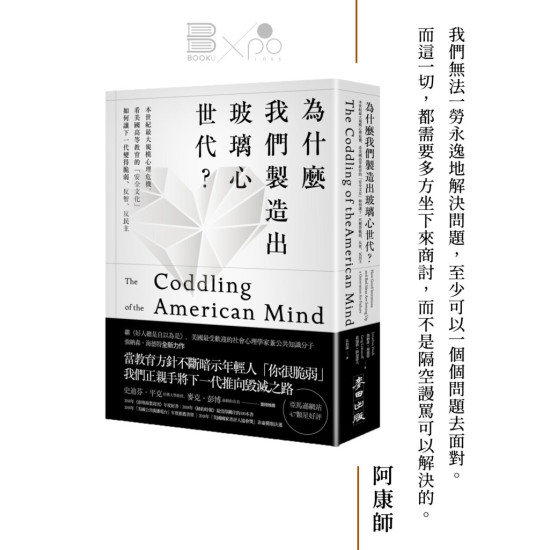
自從疫情蔓延以來,網絡上的爭論越來越多,一向很少接觸政治的我也多少看了各式各樣的評論及網絡謾罵。恰好入手了一本書《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華文書名為《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 》書中論述恰好揭開了我的迷津,我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網絡爭論,而這些爭論似乎都沒有對現實的情況有幫助。
以下我借用書中的三大概念一一解釋緣故。
1. 殺不死你的,讓你脆弱
2. 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覺
3. 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
1. 殺不死你的,讓你脆弱:
故事源自於美國的大學生們開始抵制有爭議性的人物來到校園演講。教授們也發現學生們竟然對課堂上的內容髮出抵制,原因是學生認為這些內容會傷害他們的感情,帶來負面的情感。
現時的情況也不難發現不少民眾沒有辦法接受某些訊息,進而抵制舉報,說不定這篇文章也會傷害他們的玻璃心。
大學生們要求的是 “安全至上主義”。
“我不要被任何可以傷害我的事物,我拒絕接觸來自反對一方的聲音,我全力排除這一些因素。”
在我行醫的過程裡,難免需要打針或是抽血化驗,孩童們就是比較難安撫的一群。雖然我們醫者清楚打針是為了治療,是為了病人好,可是我們的小病人是拒絕這個概念的。小孩們會哭鬧,尖叫,然而這一切都沒有幫助,只會讓他們自己的狀態更加嚴重。
看來書中的美國大學生還是處於兒童狀態,遇到不省心的事情就拼命地抗拒,並不願意聆聽並思考然後才做出決定。
他們認為,殺不死我的,會讓我更脆弱。
這些大孩子們應對著教育上的失敗。我們應該要讓孩子做好上路的準備,而不是準備好路給孩子。
《黑天鵝》一書的作者在另一本著作《反脆弱》深刻地描述了這個現象。反脆弱的概念在於一件脆弱的事物,經歷反复的失敗,吸取失敗的經歷,才是真正的強大。如果接受不了失敗,就是淪落為真正的弱者。
舉個例子,有個醫學界的花生實驗,找了六百個孩童,其中一半接觸花生,而另一半則遵守安全守則,完全不接觸花生。事後的結果證明,提早接觸花生的孩童比較少發展出對花生的敏感。也有醫學界的理論說,現代孩童普遍免疫力比較差是因為減少了戶外接觸細菌的機會,並且依賴抗生素對抗疾病,所以免疫系統沒有得到良好的鍛煉。
我們需要鼓起勇氣,認真地聆聽不順耳的聲音,攝取多方面的言論資訊。有了全面性的資訊來源,在選個立場也不遲。如果是一個成人身體,幼兒思維的現代人,難免淪陷在爭吵的洪流中,不可自拔,前途喪盡。
2. 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覺:
莎士比亞說:萬物本身並無好壞,是思考決定。佛說:萬法唯心造。誠然如此,如同我的文章好壞,並不取決於我用了簡體還是繁體字,而是在看官們的眼裡。
另一個教育界的謬論是,我們要教導孩子相信自己的感覺,並從心出發。這個概念聽起來十分美好,執行起來卻是一塌糊塗。那是因為我們的感覺是可以偏移現實的。
打個比方,某大國領導人感覺注射消毒劑進入身體是可以有效解決病毒的,那就是他的感覺,你會想相信他的感覺嗎?而他也確實是相信他自己的感覺。反過來,你可以全然確定自己的感覺就是正確的嗎?當然,如果你認為你的另一半出軌,不妨學學周揚青,說不定會有驚喜。
醫學界裡,治療精神病的除了藥物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療法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認知行為治療。
當我們處於情感的領域時,難免會有不切實際的推理和感受,例如Castrotophing trend 極端式推理,開始推理出由於今天不吃早餐而造成腸胃不適,然後會腸道出血,接下來就快死了,或者是男友不回我信息,肯定是在和別的女人聊天,不行,我一定要先發製人,立刻分手。
或者是 Emotional Reasoning 情緒推理,任由感覺引導你對現實的詮釋。我感到很悲傷,我的人生就是一個悲哀的笑話。我覺得很憂鬱,我的婚姻一定會失敗。
還有 Over generalizing 以偏概全,他看中國戲劇,一定是中國人。他吃辣,肯定是辣手摧花。他喜歡抖腳,一定會敗光家產。
這一切都是認知行為治療可以幫助到的感覺偏見。我們賴以生存的感覺系統是自石器時代的遺留。如果你看了諾貝爾經濟獎得主 Daniel Kahneman《快思慢想》一書,必然會對上述話題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我們的感覺並不可靠,尤其是當我們有過激反應的時候。
每逢大事有靜氣,當我們被一件事物激起萬般情緒時,不妨訓練自己代入理性思考的一端,先仔細思考,再做決定,這一點在購物上來說尤其有用,男士們可以思考一下要不要分享給另一半。
3. 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壞人:
二元論的善惡觀是很方便的一種思維方式。世上便分類了男人女人,葷食素食,美國快餐和法國慢食,如此種種不計其數。
而道家有言:天地不仁,視萬物如芻狗。這茫茫天地之間本來就沒有善惡好壞之分。
人類的善惡論要追尋到遠古宗教——拜火教 Zoroastrianism。在拜火教教義裡,善神創造了人的靈魂,而惡神創造了人類的身體,而教義教導人類要幫助善神打到惡神,為宇宙的安定出一份力。
為何拜火教的教義如此深得人心,以至於世界上大部分的成功宗教都有類似的言論呢?這是因為遠古的人類是實行部落主義的。
例如黃體戰蚩尤便是兩個部落之間的紛爭。那時候的人類只有遵從部落主義才可以生存。你不是我部落的人,我便可以聯合我的部落來搶占你的資源,不屬於任何部落的,將得不到任何幫助,以至於滅亡。
將時間拉長到二戰時期的德國,希特勒便是利用了人們的部落主義群體,將雅利安人規劃為一個善的群體,而猶太人則是惡的群體,淡化了雙方都是人類的事實,進而實行殘酷的滅絕計劃。部分的德裔軍官在事後的審判中供認,他們並不認為他們是在屠戮人類,因為清掃猶太人已經被視為他們的義務。
當我們信賴部落主義,沉迷於自身的同溫層中,將世界分為好人壞人的同時,我們往往忘了應以善意來理解他人的言論。
書中《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的大學生們將自己塑造成了受害者,也將持反對意見及任何不支持他們的人視為壓迫者。這一行為和榮格的心理學不謀而合。
我先前閱讀榮格的情緒陰影理論時,發覺我們喜歡將自己代入各種性格原型。榮格的理論說情緒陰影是心靈深處的雜質,當我們有特定的經歷時,便會加強情緒反應,並代入虛擬的角色,彷彿上台的演員,陷入角色無可自拔。
其中一個情緒陰影就是受害者角色和壓迫者角色。
但學生們講自己代入受害者角色的同時,他們必須維持一個受害的狀態,所以便將所謂“壓迫者” 的任何行為都詮釋為對他們的加害,並且學會忽略別人的動機,只重視自己所受的影響。
這樣一來,矛盾只好不斷累積,受害者們也得以保留自己受害者的地位。這類的行為並沒有實質的意義,只會阻撓解決方案。所以說,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想必就是這類的人吧。
總結:冰厚三尺,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社會上的撕裂不是因為一場疫情造成的,而是種種因素之下所醞釀出來的現象。我們無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至少可以一個個問題去面對,商討解決方案。而這一切,都需要多方坐下來商討,而不是隔空謾罵可以解決的。
我寫文章一般來說都是一氣呵成,且不審稿,所以有引用得不對的地方或是疏漏之處,敬請原諒。
#BooKu
#品系
#星期二深夜專欄
#阿康師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