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庖丁解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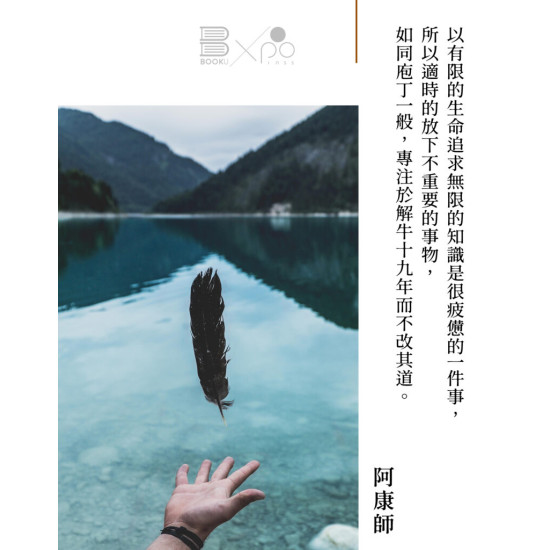
當我們想要深研莊子時,從庖丁解牛開始也不失為過。我將在文章中論述養生,養心性的道理,以莊子之道養心修行。而這篇故事也比較大眾化,適合作為一個入門級的探討。
原文: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解:莊子善於揶揄儒家。當儒家言君子遠庖廚的時候,莊子特意的寫了這樣一個故事,修行不關職業身份地位,因為萬般皆是道理,佛有八萬四千法門,道有三千六百旁門,須知種種皆有訣竅法門,都有修身養性的道理。
而文中梁惠王觀察庖丁宰牛的方法,驚覺庖丁的動作無異於典雅古樂的演奏,宰牛也如同奏樂一般優雅,究竟是何故?可以將宰牛這樣粗俗血腥的場景演變得如此高尚,不也是道的體現麼?
原文: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解:庖丁告訴梁惠王,我追求的是道。
莊子的逍遙之道可以在宰牛中體現,並不限於朝堂之上,也不限於大雄寶殿之間,而在於生活中,不被身份所拘束,即是擺脫了世俗的拘束,也擺脫了我們自身的成見。
廚師屠夫在古代是屬於比較低賤的職業,所以儒家的理想在於樹立君子的模式,而莊子的理想在於逍遙,我們能從這則故事的主角中看到,這是一個身份低賤的屠夫和高貴的帝王對話的情景。屠夫可以自在自信的和高高在上的帝王說話,講解他屠宰的心得,而不是唯唯諾諾低頭稱是,在心態上,屠夫是逍遙的。
而庖丁繼續講解了他宰牛的經歷。剛開始他看到的是一頭牛,三年後他看到的已經不是完整的牛了。為何如此呢?因為他不再以眼睛來看,而是以心眼來感知這一頭牛。
從庖丁的角度來說,起初他看到的牛隻是牛,而後當他逐漸深入了解並開明心性的時候,這頭牛並不是完整的牛,而是已經庖解開來的牛的各個部分。
而庖丁是如何達到這個境界的呢?他捨棄感官,以心神來體會牛的構造,找到了筋骨相連的縫隙,輕輕拿刀劃過,刀子甚至不受到磨損,宰了十九年的牛,刀子還像新的一樣。雖然已經經驗豐富,可是每當遇到比較麻煩的部位時,還是會提高警惕,輕輕一拉,牛便肉骨分離。
心性明了的莊子展現了不受外在形式拘束,明心見性,達到事物的本質。捨棄感官如同斷五蘊,亦如『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所示 “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慾不生,三毒消滅 ”。
做完這一切,他方才悠然而立,怡然自得。這宰牛時精神警惕的狀態瞬間就放下,轉換為合適的輕鬆心情。
莊子所訴說的便是張弛有度的道理。試想我們常帶著工作時期的煩躁心態回到家裡,影響了生活的質量,如果我們學習庖丁該專心的時候專心,該輕鬆的時候輕鬆,那么生活中許多壓力的問題不是迎刃而解了嗎?
最後,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解:以有限的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識是很疲憊的一件事,所以適時的放下不重要的事物,如同庖丁一般,專注於解牛十九年而不改其道。以逍遙自然的心態做善事而不圖名利,也不因為為了順著本心行事而犯罪,遵循自然中正的道理,自然可以保全身性,享盡天年。
莊子的智慧遠不止這一篇文章,不論是在養生,修行心性,做人道理和對待他人的方式上,我們都可以從莊子中找到合適的答案。礙於篇幅不能逐字逐句研討,留待日後再作功夫。
#BooKu
#品系
#星期二深夜專欄
#阿康師讀書
